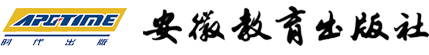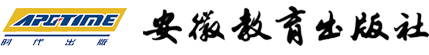本书以文本阅读的方式对罗兰·巴尔特的理论进行了地毯式的清理,明确了“中性”作为方法和策略在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追溯了这一思想的语言学来源,以及它对巴尔特的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和生存美学的影响。本书将讨论的范围拓展到了巴尔特的跨国旅行以及他所关注的音乐、摄影和教育领域,并且将他的晚期研讨班作为研究的重点,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
 样章试读:
样章试读: 前言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笔耕不辍,写下了卷帙浩繁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的独创性和思想性,使他和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等人一样,赢得了世界声誉。时至今日,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对不同国家的理论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鉴于巴尔特的重要性,格雷厄姆·艾伦评论说:“要研究当代理论,必须从了解和研究他的作品开始。”可是,面对如此繁复的作品我们该如何理解他呢?这是每个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在一本小书中告诫我们,巴尔特拥有“变色龙”一般的理论个性:“每当巴尔特想采取一些新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创建文学科学、符号学、当代神话科学、叙事学、文学意义史、分类学、文本愉悦的拓扑学——他又会迅速转向其他方面。他经常放弃曾经固守的提议,并且在写作中对自己先前关注的事物冷嘲热讽。” “这种情况可能会让读过巴尔特某部作品,并且被其灼见激动过的人感到不满。人们往往责备巴尔特缺乏坚毅的性格,转而赞赏那些在葡萄园中踏实苦干的人,他们不会被天边诱人的景色吸引而逃避劳作的艰辛。但是,巴尔特令我们兴致盎然,因为他富有刺激性,我们很难将自己对其作品的迷恋与他不断求新求变、突破传统的行为分开。对某些计划的持久献身可能会使巴尔特成为一个创造力低下的思想家。”因此,当我们企图定义巴尔特的身份,称他为——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一个作家、一个文学评论家、一个符号学家、一个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者、一个文坛斗士、一个同性恋者,都会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安迪·斯塔福德(Andy Stafford)在自己的著作中半是认真半是戏谑地说,巴尔特的名字是加了复数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理论上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巴尔特,存在的是数个巴尔特的叠合。他们分散在不同的文本中,彼此参照,相互折射,进而形成色彩斑斓的理论风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在不断地阅读他。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研究者胆敢声称自己的阅读是详尽且切近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巴尔特的理论非常混杂,更是因为其作品呈现出来的独特风格。凡是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品大多行文跳跃,语义艰深,既含沙射影,又飘忽不定。在形态上,非常接近于他曾定义的“极乐的文本”(text of bliss):“这种文本处于眩晕的状态,令人不适(或许已经到了厌烦的地步),它拆解了读者的历史、文化和心理预设,破坏了他的趣味、价值和记忆的连续性,使他和语言的关系陷入危机之中。”更何况,他的作品总是装配着各种时髦的理论和科学的伪形,如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如果我们对这些理论亦步亦趋,那么,又不免会滑入巴尔特极力反对的“多格扎”(Doxa,又译“套语”“套话”“陈词滥调”)。在他眼里,“多格扎是一种错误的对象,因为它是死去的重复,它不是来自活人的身体——更确切地说,它来自死人的身体”。作为一种反应性训练,巴尔特总是不断地寻求悖论(Paradox)。当一个多格扎出现了,为了摆脱它,他假设一种悖论。当这个悖论又成为新的多格扎,他又抛弃它,重新寻找新的悖论。从多格扎到悖论,再从新的多格扎到新的悖论……如此循环,致使巴尔特的理论总是处于未定和流变的状态。在一些著作中,他还特意提醒人们“不要去相信他所写的东西,而要相信他所作出的写作的决定”。这些无疑令卑躬的学者们心生敬畏,却又欲罢不能。于是出现了十分有趣的现象:人们总在滔滔不绝地说他,可是又有谁能摸得准他呢?
有学者评价雅克·拉康是“一个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理论家”,和他同在一个阵营并且相互亲近的巴尔特又何尝不是。特别是转入后期,巴尔特的写作更是无所顾忌。“他混融一切语言,即便这些语言不能相互匹配;他默默地接受各种指责,非逻辑性,非协调性;面对苏格拉底式的讥讽(让对话者颜面无存:自相矛盾)以及合法的恐怖主义(多少罪证就是建立在连贯性的心理学的基础上),他漠然置之。这样的人当然是被我们社会——法庭、学校、收容所——所嘲讽的对象,人们对他不屑一顾:谁能寡廉鲜耻地忍受得了矛盾?现在,反英雄(anti-hero)出现了:在他自得其乐的时刻,他就是文本的读者。”这不仅意味着巴尔特是站在传统的对立面来展开写作,而且从源头上混同了作者和读者,因为在他的眼中,读者并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主动的生产者,他和作者一样总是积极地参与文本的生产。“打开一个文本,将它置于阅读的系统之中,不仅仅是要求并展示它能够被自由地理解;更重要的,而且更为彻底的,是为了获得一种认知:不存在阅读的客观的或主观的真理,而只有游戏的真理;在这,‘游戏’不能被理解为娱乐消遣,而必须被理解为一项工作——然而,在这项工作中,劳作的艰辛烟消云散了:阅读就是使我们的身体活跃起来(精神分析教导我们,身体大大超越了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意识)。在文本符号的邀请之下,语言来回地穿越我们的身体,并且形成某种波光粼粼的句子的深渊。”假如人们尚未找到进入巴尔特的方便之门,这段文字便启示我们:何不将他视为“可写的文本”?
所谓“可写的文本”(writerly text),具有这样的特性:首先,它并非现成之物,我们不可能在书架上找到它,从一开始,它就隶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其次,它是生产性而非再现性的,这种对立很容易让人想起拉康对“真相”(real)和“真实”(reality)所作的界定,前者是“演示”出来的,而后者是“显示”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了第三个特征,即它总是延宕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能够吸引不同读者积极参与其中;最后是它的差异性或者复数性质,可写的文本追求的不是某种特定的、不变的语义,而是诸多意义的交响。面对这样的文本,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解释进行不断的修改调整,然后再次潜入文本之中,从而获得更新的理解。总之,“在这种理想的文本中,不仅网络纵横,而且交互作用,没有一个能够超越他者;这种文本是能指的星系,而不是所指的结构;它没有开端,可以往复回流;我们可以获得无数的通道,却没有一个胆敢宣称自己是主要的;目力所及,符号不断向前延伸,它们是未定的(意义从来不受限于既定的法则,除非通过丢骰子的方式);意义的系统可以接纳这种绝对的复数的文本,只要语言具有无限性,那么,它的数目就是无尽的”。
日本学者铃村和成在“挺近”巴尔特时曾确立了以下原则:一、不将巴尔特神化;二、不自诩为巴尔特研究的专家;三、仅限于做个普通读者来阅读巴尔特。我认为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这些原则仍值得借鉴,不过在方法上还应补充一条,即可大胆地将巴尔特视为“可写的文本”。本书就是以上四种原则指导下的产物,也就是说,我对巴尔特的阅读实际上是一种个性化的写作。这种写作并非为了逃避责任,摆脱逻辑梳理和历史阐释的艰辛,而是为了寻找一种更加切近巴尔特的方式。回到巴尔特,这既是我也是同时代读者的梦想。
在本书的结构安排上,我没有依循通常的做法,即按照章节的顺序来布局,因为这种布局方式讲求的是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和整体性。这样做显然与巴尔特的思想背道而驰,凡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理论创建的过程中,特别是转入后结构主义阶段以后,极力反对的就是逻辑性和整体性。在《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1975)一书结尾,他就讥讽整体性同暴力那样滑稽可笑。为此,我不仅略去了“第一章”“第二章”这样的提示语,而且放弃了整体性的幻觉,将这些片断随机地搁置在一起,它们就像一个个文本的入口,当您拿起这本书,无需从头至尾地阅读,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在每一个片断以及这些片断与片断的裂口处,您将会看到巴尔特如此斑斓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