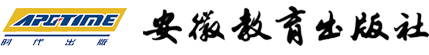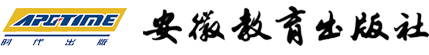ISBN:978-7-5336-8648
作者:胡亮
出版时间:2018.9
版次:
印次:
装帧:
定价:58 元
本书收录了诗人、批评家胡亮近年随笔十三篇,涉及大江健三郎、金斯伯格、纳博科夫、敬隐渔、纪弦、孙静轩、海子、苏小小、现代性、八十年代诗歌、诗人之死、截句写作等作家、作品与相关话题,融合了文论、游记、史传等多种文体,显示出作者广博的文化视野、炽热的知识兴趣和独特的批评风格。
读胡亮的文章有一种欣慰,觉得我们的事业有大希望。我寄意于年轻一代的正是如此:希望,且超过我们。
——谢冕(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胡亮的文论和诗性随笔眼界开阔,功夫扎实,细节娴熟,笔墨清扬,有考据,亦有文体,别有身段、风姿和气韵,这么好看,的确让我刮目相看,也真心推荐给大家看。
——柏桦(诗人,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胡亮的文字充满灵性,他以诗人心态从事诗学批评,自然能见到职业批评家见不到的东西,予人以莫大的启示。胡亮是当下拯救诗学批评于低谷甚或绝境的少数人物中的一个。
——敬文东(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胡亮,生于1975年,诗人,论者,随笔作家。著有《阐释之雪》(2014)、《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2015)、《琉璃脆》(2017)、《窥豹录: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2018),编有《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2015)。创办诗与诗学集刊《元写作》(2007)。获第2届袁可嘉诗歌奖(2015)。现居四川遂宁。
大江健三郎书店
两个金斯伯格
谁的洛丽塔
——洛丽塔诗学的叙述学分层
你是谁,为了谁
——关于新诗现代性的札记
可能的七里靴
——介绍敬隐渔的诗与译诗
“且去填词”
——读《纪弦回忆录》
孙静轩
“白金和乌木的气概,一种混血的热情”
——重读《青年诗人谈诗》
“隐身女诗人”考
——关于若干海子诗的传记式批评
诗人之死
也来谈截句
回到帕米尔高原
——亚洲腹地的诗歌之旅
遇真记
——苏小小接受史小纲
后记
内文节选
“隐身女诗人”考
——关于若干海子诗的传记式批评
野鸽子
——这黑色的诗歌标题 我的懊悔
和一位隐身女诗人的姓名
——海子《野鸽子》
一
近年来,海子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举凡思想探析、文本读解与传记写作,均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已有多位学者以此鸣世。然而,“隐身女诗人”案一直是难以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海子的几位传记作者,要么陷入迷雾,要么妄自猜想,要么绕开困局,均未能给出准确的答案。本文则试图在相关研究中有所突破。当然,我的目的,乃是重新启用“过时”的传记式批评(Biographical Criticism),更有效地阐释海子留下的一系列相关作品。揭秘与猎艳,固非本人之志趣也。
二
1988年5月16日夜,海子完成了一首七十七行的短诗《太阳与野花》,特别标明“给AP”。在海子所有作品中,这一件,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来,都显得十分特别。如果单单考察其形式感,我们马上就会震惊于全诗中人称的错乱与清晰。是的,只能这样评价:错乱与清晰!比如,第一行的“他”,第三行的“我”,第三十八行的“海子”,都如此确定地指向了太阳,亦即抒情主体;第二行的“她”,第三十二行的“你”,都如此确定地指向了野花,亦即抒情对象;而第三、四、六行的“你”,拥有一个樱桃的母亲——樱桃,已经明显偏离野花之于落寞、低贱、素洁和“竟岁无人采,含薰只自知”的意义指向——这肯定意味着全诗在主题和主角上的旁逸斜出;至于第二十二行的“你”,相当男性化,无疑已是泛指。毫无疑问,诗人同时拥有多个视点(Point of View),并在这些视点之间游移不定,终于构建出繁复摇曳的叙事学:他有时候使用全知之眼,看到“太阳是他自己的头/野花是她自己的诗”,甚至发现了海子“自由的尸首”。有时候使用半知之眼,比如太阳之眼,以观野花,“你们还可以成亲/在一对大红蜡烛下”,又如野花之眼,以观太阳,“去看看他 去看看海子”。海子曾经说过,诗歌不是修辞,而是一团烈火。此诗中视点的频繁转换,显然并非出于形式主义的穷讲究。之所以不得不如此,乃是因为海子同时叠加了生命中几段不同的情缘,“在技术处理上还存在着一个意象上另一个意念的附着、覆盖,以及退出,这样一层层的丝膜错杂”。读罢全诗,我们会发现作者的一条附注:“删86年以来许多旧诗稿而得。”由此亦可见,此诗绝非一时一地一人一景之作。因此,与其说是视点的频繁转换,不如说是视点的仓促集结,乃至最终不能归于一统。
樱桃女儿,海子在日记和诗歌中均称之为B,乃是中国政法大学1983级学生,来自内蒙古,父母均为高级知识分子,后来成为海子的初恋,并设法在《草原》上发表了后者的若干作品。海子曾为之写下不朽的诗篇:《给B的生日》。但是,正如《太阳与野花》所显示的,“你的母亲是樱桃/我的母亲是血泪”,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最终导致两人早早分手。1986年10月,海子在《泪水》一诗中写道:“在十月的最后一夜/我从此不再写你。”这场绞机般的爱情几乎粉碎了诗人的心,同年11月18日,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一生中最艰难、最凶险的关头。我差一点被毁了。”接近两年之后,B又出现在《太阳与野花》的开端,虽然一闪而过,亦可见海子之念念不忘。但是,很显然,B仅仅是此诗的一个序言:为了后文中AP的正式出场。
然则,AP何许人也?燎原认为,AP实为两人。细细考察《太阳与野花》,全诗不同处确有差异化的表达,明显存有多重指向;第二十行:“两位女儿在不同的地方变成了母亲”,则提供了较为明确的信息;另有一个外围事实,海子向以单个拉丁字母,比如B、S,指代其生命中的重要女性,亦可作为这个观点的参考。据燎原等人研究,P是海子的一位同事,已婚,有孩子,其老家应在青海德令哈。海子于1983年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第二年就在《不要问我那绿色是什么》一诗中写及青海湖。在《太阳与野花》定稿半年后,海子又完成一首《无名的野花》,再次在一种致幻般的氛围中,写及青海湖边的野花、大草原上的恍惚的女神。同一时期还在多件作品中写及青海公主,可能就包含着对于P的臆想。1988年7月25日,海子坐火车经青海德令哈,写下那首肝肠寸断的《日记》:“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显然就是献给P的呓语。燎原进而指出,P即是《野鸽子》一诗中的“隐身女诗人”。《野鸽子》完成于1988年2月。同年同月完成的另外一首诗《一滴水中的黑夜》,“野鸽子”再次出现,并与一位“女王”构成互涉,“这些陌生人系好了自己的马/在女王广大的田野和树林”。在海子的心理指认中,P是一个姐姐,好比导师,A是一个妹妹,接近情人。《太阳与野花》有句:“是谁这么告诉过你:/答应我/忍住你的痛苦/不发一言/穿过这整座城市/远远地走来/去看看他 去看看海子”,就明显出现一个三角关系:善良的P最懂得海子的孤独和绝望,她把解救的希望寄予A。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P是一位诗人,她最多只是海子才气的“欣赏者和引导者”。
必须附带说明的是,B和S亦非诗人——B尚能欣赏海子诗,S则对海子诗可能带来的现实龃龉抱有极大的担忧。
三
边建松认为,《日记》一诗原本献给西藏女诗人H,则又不准确。因为还要在完成此诗数日之后,海子才翻越唐古拉山,在8月初到达拉萨,初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H。如果单从内容来看,《日记》的悲伤、孤独和空荡,则又与H坚拒海子莽撞示爱的事件构成了严丝合缝的呼应——或许,在见到H之前,忐忑不安的诗人就隐约预知并提前领受了这种悲伤、孤独和空荡?H年长海子近十岁,与后者密友骆一禾交厚,此前可能与海子有过书信往来,当时离居拉萨,与一条大狗相伴。可能以其品性芬芳、思想纯净、境界高远,燎原借用马原一部小说的书名,称之为“拉萨河女神”。她能够与燎原等坦言海子夜访事,亦可见其胸襟。她的名作《我的太阳》,以及散发出来的边地文化气韵和成熟女性魅力,对于以“太阳”自许的海子来说,构成了强烈的召唤。H似乎已经成为最大的嫌疑。但是,她亦不可能就是那位“隐身女诗人”。因为在见到H之前半年,海子就已经完成《野鸽子》一诗。
四
剩下来的,需要被证明的,只有A。A已经与“隐身女诗人”重叠在一起。现在,我们必须循着另外一条线索继续从头起步。
1987年8月,海子完成《十四行:玫瑰花园》。很明显,此诗隐藏着诗人与某女诗人彻夜谈论但丁及贝亚丽丝的本事。诗人写道:“四川,我诗歌中的玫瑰花园/那儿诞生了你——像一颗早晨的星那样美丽。”我们已经在青海和西藏陷得太久,现在,必须依照海子本人的指引,由西北而西南,来到另一块土地。
在其短暂一生中,海子至少两次进入过四川。
第一次是在1987年1月。他乘坐北京直达成都的列车,未至成都,便在广元站下车,然后换乘汽车,去了川北藏区九寨沟,继而折回,来到川东北山区的达县盘桓数日后,乘汽车赴万县,换乘江轮,顺长江而下,回到安徽安庆。九寨沟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坎前边缘区,作为旅游圣地,现在已经驰名于世界。然而,九寨沟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区,却迟在1984年;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则迟在1992年。1987年,九寨沟尚处于保护区向旅游区的过渡期,名气不甚大,人迹不会多。1月,正是体验九寨沟冰雪世界的最佳期。海子此去,或如燎原所言,乃是为了朝拜诺日朗:想来诺日朗瀑布已然冰冻,而诺日朗雪山当更加晶莹——1983年5月,杨炼在《上海文学》发表组诗《诺日朗》以来,此诗就一度成为诗歌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并引领了当代诗歌史文化地理向度上的史诗写作潮流。很多四川诗人,比如宋氏兄弟、廖亦武、石光华,部分的翟永明和欧阳江河,都是后起者。我们的海子,也正是声气相通的后起之秀。巧合的是,在九寨沟的山谷森林之间,镶嵌着数以百计的湖泊,犹如镶嵌着一块块蓝水晶。当地人就称之为海子。海子此去,或为与若干海子聚首亦未可知。这种地气上的契合感,引导了海子最后的行踪。经查,1987年10月,海子曾忆写有《九寨之星》一诗。此诗仅有八行,抒情对象之人称,迅速由第四行的“她”转变为第七行的“你”。值得注意的是,海子把九寨沟的海子喻为女神点亮的一盏灯,却把“你的一双眼睛”喻为镜子中的两盏灯。这颗九寨之星,是否就是两个月前在《十四行:玫瑰花园》中曾经出现过的那颗星?不管怎么样,海子的九寨之行,隐约出现了一位女性。当他到得达县,写下《冬天的雨》,这位女性已经逐渐清晰:“一只船停在荒凉的河岸/那就是你居住的城市。”那么,海子此行,乃是去见当地一位年轻的异性朋友?这个观点的确立,有赖于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海子去见正在老家度寒假的徐永。徐永,男,诗人,1965年生于四川万源,北京大学中文系1983级学生,以《矮种马》一诗享誉校园,曾任“五四文学社”社长、《启明星》主编。徐永进校前,海子已毕业,但是两人相熟则无疑问——均在1986年,前者写下《竹篮》,后者写下《鱼筐》,亦即著名的《在昌平的孤独》,表现出相似的题材攫取和不同的情感皈依。万源与达县毗邻,今同属达州市辖。然而,经徐永回忆,他绝未与海子在达州见过面——他甚至不知道海子到过达州。可见海子一直保守达县之行的秘密,其目的,可能正是帮助某个人“隐身”。然而,这秘密最终还是被他自己的作品泄露:《冬天的雨》,以及《雨鞋》,明确标明写于达县——从所署时间来看,海子至少在达县停留两天,从当月11日至12日。另一件作品——《雨》,被海子另一位密友诗人西川,认为大概就是《冬天的雨》的重写稿或改定稿。这些作品径用第二人称“你”,明显地隐藏着若干本事:特别是与一个“仙女”雨中共伞的本事。《冬天的雨》中诗人“随身携带的弓箭”后来再次在《太阳与野花》中出现,“一张大弓、满袋好箭”。而在完成《九寨之星》的同时,海子还完成了一首《野花》,提及一位“雨和幸福/的女儿”。综合考察这些信息,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把这里的“你”与A重合为一人。《雨鞋》则显示,此前海子与A曾有通信。据多人研究,此行中,海子曾与A同游达县境内的州河及七里峡真佛山。回到安庆后,海子写有《给安庆》一诗,有“可能是妹妹/也可能是姐姐/可能是姻缘/也可能是友情”之句,泄露了他对S与A的感情预期。海子离开四川后不到五个月,他的作品《献给韩波:诗歌的烈士》、《水抱屈原》、《但丁来到此时此地》发表于达县《巴山文艺》第6期“启明星诗卷”——经考证,这次发表机缘的促成,正是徐永及其朋友——另一位达州诗人凸凹——的努力之功,可能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但丁来到此时此地》一诗中,海子写道:“树桠裂开,浅水灌耳/在香气的平原上/贝亚德丽丝/你站在另一头,低声歌唱。”贝亚德丽丝就是海子在《十四行:玫瑰花园》中写及的贝亚丽丝。在1986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海子使用的则是王维克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翻译《神曲》的译名:贝亚德。贝亚德丽丝,这个佛罗伦萨少女,在九岁时引发但丁的爱情,当其二十五岁夭死之后,就一直是但丁诗篇中永恒的女神。海子在《巴山文艺》选发《但丁来到此时此地》一诗,已然自视为但丁,并将A视为贝亚德丽丝,亦即此诗的收件人,其苦心与深意自不待言。
第二次是在1988年3—4月。海子陪母亲游览北京后,怀揣尚未完成的长诗《太阳》,直奔成都,先去川南,观瞻乐山大佛,并在沐川宋氏兄弟的房山书院盘桓十余日,继而回到成都,先后住在诗人万夏和尚仲敏处,并与欧阳江河、翟永明、石光华、刘太亨、廖亦武、钟鸣、杨黎等见面,还曾当众朗诵廖氏《大盆地》一诗,盘桓数日后方回北京昌平。很显然,这是一次诗歌之旅。四川诗人,特别是整体主义诗人,带给海子生活的、诗学的——暖意,让他刻骨铭心。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在成都期间,海子可能有过约会。此行结束回昌平后,4月23日,海子即写下《跳伞塔》一诗——跳伞塔,乃是成都市区一个小地名——“我在一个北方的寂寞的上午/一个北方的上午/思念一个人”。这首诗的第六节共有五行,则更为重要,“已经有人/开始照耀我/在那偏僻拥挤的小月台上/你像星星照耀我的路程”。几天之后,时间来到5月,海子又写下《星》,“星/我是多么爱你”。这里的跳伞塔之星,旷野之星,是否也就是八个月前在《十四行:玫瑰花园》中曾经出现过的那颗星?如果是,A或曾赶赴成都与海子见面亦未可知。在沐川期间,宋氏兄弟中的宋炜曾为海子算过卦,言及海子的诗已然形成一个黑洞,要将他吸将进去;又言及,海子在成都有一个女友,今后不会在一起。第一卦显然应验;第二卦不知准确否,却影响了海子传记作家燎原,后者认为A老家在达县(该县毗邻神农架),毕业于北京某大学,工作于成都某医科大学,并称之为“神农氏之女”,云云。另一位传记作家周玉冰,显然受了影响之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海子与A的两次交往均作了绘声绘色的文学性摹写,并将A称为“安妮”,工作单位则由一所大学变成一家医院。大学而兼医院,难道是指华西医科大学?倘若真的如此,海子或另有所遇——在完成于1988年8月的《雪》中,明显可以看到,“草原”和“成都”,都是海子的情感寄托地。
或以为在1989年初,海子曾第三次来到四川。然而证据不足,可能乃是误记。
五
海子另有一件作品《病少女》,完成于1987年2月,即离开达县的次月。此诗写及一家三口为他送行的情景,特别写到一个小姑娘,“病少女 清澈如草/眉目清朗,使人一见难忘/听见了美丽村庄被风吹拂”。很多论者以为,一家三口即是A的一家三口。那么,A是病少女母亲还是病少女本人呢?这个问题颇难回答。边建松就否认《病少女》与A有关;但是,边氏同时认为,此诗是经验综合的结果,不一定确有其事,则又未必。1988年2月,海子《大风》诗中又出现了相似意象:“想她头发飘飘/面颊微微发凉/守着她的母亲/抱着她的女儿/坐在盆地中央/坐在她的家中。”奇怪的是,此诗之地理信息再次指向四川。病少女一案,或者另有本事亦未可知。真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六
1989年的春天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我们当然会发现,在此期间,海子连续写下《太平洋上的贾宝玉》、《献给太平洋》、《太平洋的献诗》,牵肠挂肚于在一年前就已经移居海外的B。但是,同时,海子还写下《桃花》(共二首)、《桃花开放》、《你和桃花》、《桃花时节》、《桃树林》,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A。无论这个直觉准确与否,都不影响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海子对A的幻想和创造仍在不断膨胀。3月9日,在自杀前的第十七天,他删定当年1月就草成的诗稿:《月全食》。“月”,自然是“星”的演绎——如前所述,此类意象已经被海子写为系列作品,埋藏下重要的线索。这首诗开篇就写道:“我的爱人住在县城的伞中/我的爱人住在贫穷山区的伞中/双手捧着我的鲜血”,无不与达县之行及《冬天的雨》、《雨》、《雨鞋》等诗中的诸多细节相吻合、相映射。唯“我的爱人”一语,可能是万念俱空之后的谵呓,也有可能是撒手之前的闪念,剩下来的唯一稻草:海子藉此暂时漂浮在世俗的水面上。但是,决心已定,舌头颤抖,斧头闪现,空气紧张,死神的脚步已然戛戛而来。海子已经看到自己的鲜血,他希望最终由A用双手捧着他的鲜血。
七
那么,A是不是一个诗人呢?
根据边建松的研究,AP实为一人,就是A。边氏曾得见并引述过A写给海子的信件。这些信件分别写于1987年1月海子去达县之前和1988年4月海子回昌平之后,据边氏摘引的部分内容可以判断:A长期住在达县,工作与算盘和数字有关,闲时尝试着写一些自白式的诗歌,对海子的一些作品也不是太懂,曾邀请海子去达县一游,并对后者抱有某种情感上的期待——这是海子第一次四川之行选择那样一条奇怪线路的重要原因。两人的现实关系,应该处于倾慕与克制之间。换言之,最后中断为遥远的友情。
据此可知,A有可能即是达县女诗人D。D,生于1967年,中专毕业,专职会计,业余写诗。与海子交往时,年仅二十岁,小海子三岁。近年来,D完成了较多作品。对阿拉伯数字的敏感屡见于《辞职报告》、《求职书》、《任命书》、《计数器归零》诸诗。曾写有多篇作品,比如《州河,女人与瓦罐》、《我声音多么卑微》、《蝉音》,纪念其在州河及七里峡真佛山的行踪。让人惊异的是,D也写下为数不少的桃花诗,似在与海子相酬唱。在《又见桃花》中,出现了“牧羊人”,与《太阳与野花》中海子对A的祝福,“那个牧羊人/也许会被你救活/你们还可以成亲”,也构成了呼应。但是,也许D并没有领受海子这种了犹未了的祝福,多年以后,她写下《行船调——写给自己的生日献词》一诗,再次忆及这一折“躺在诗歌里的爱情”。2009年,海子逝世廿载。在上一年的春天,D自言,当她看见那些抽穗的麦苗时,不禁悲从中来,当即写下《最后的诗章——给海子》,“既然,在这三月无法让文字欢愉/那么,让曾经的美丽,风干的记忆/谱写一曲最后的歌谣”。近来,D另有《空白》、《三月,不敢想桃花》二诗,亦为纪念海子,或者说想念海子之作,风格朴实真切、直白深挚。D在自己的诗中特别提及海子的《女孩子》,应予特别注意。《女孩子》,不详何年所作,有“她用双手分开黑发/一枝野樱花斜插着默默无语”之句,与《冬天的雨》中一些诗句颇有牵连,“这都是你的赐予,你手提马灯,手握着艾/平静得像一个夜里的水仙/你的黑发披散着盖住了我的胸脯”。D还有一诗,《在暮色中静下来》,虽未明确标示为海子而作,但是似乎具有更为清晰可辨的海子风,对面隐藏着一个再没有比海子更合适的聆听者,“亲爱的人,如果有一天我听不见你的声音/我是幸福的/如果有一天,你读不到我的眼神/你,也应该是幸福的”。
为进一步求证,笔者对假设当事人进行了短信采访。据D答复:早在1987年,她便知道海子,并尝试写作;后来中断二十年,直至2007年读到大量海子作品,才重拾诗笔;她视海子为诗神,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将“你”设定为海子;她从未与海子有过书信和现实往来,却对海子葆有“个子中等,黄黑肤色,络有胡须,深沉不苟言笑,能洞穿世事,悲悯而有大爱”的印象;她同时断言笔者“肯定在达县找不到海子见的那个人”。
世间居然有这等巧合事。
八
达县还有两位女诗人:T和L。T生于1974年,夭于1993年。此女虽然甚有才华,然而1987年尚不足13岁,想必还不能与海子对谈但丁——愿她在天之灵得聆海子哥哥的诗教。L出身书香,写诗,画画,据闻美丽不可方物。有关信息显示,其年龄甚或比T更小。
舍此,达县再无女诗人矣。
九
“我不能忍受太多的秘密/这些全都是你的”,海子在《月全食》的最后一节如是说。不能忍受的已经离世,愿意忍受的始终缄口:这个问题恐怕将难以解决。
真是完美无缺的隐身。
当然,我们的思考也许还应该存有另外的向度。1986年8月,海子在一篇类似诗学断片的日记中写道:“其实,抒情的一切,无非是为了那个唯一的人,心中的人,B,劳拉或别人,或贝亚德。她无比美丽,尤其纯洁,够得上诗的称呼。”由此可见,在海子看来,他生命中的重要女性似乎都可以称之为“隐身女诗人”。
既然如此,哪怕A终于现身揭秘,我们也不能理直气壮地指认,只有A,才是那位“隐身女诗人”。
十
现在必须归结到海子的《四姐妹》上来,“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四姐妹,不多不少只有四姐妹——在B、S、P、A、H之中,海子剔除了谁?我有一种感觉:如果P确实存在,他剔除的应该是H。
十一
这篇胶柱鼓瑟、捉襟见肘的传记式批评就要煞尾了。我认为,传记式批评之本意,绝非将个人化隐私上升为历史性问题。恰恰相反,与一切文本中心主义者相接近的是,传记式批评的前提和原则,虽然还不是文本(Text)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足性,但是最终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我深有体会的是,一些文本的幽深与陡峭之处,无论怎样细读(Close Reading),都难以求得合乎逻辑、令人信服的阐释。而传记式批评一旦介入,这些看似蹊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切都有因由:千般玄妙都来自柴米油盐的真实颗粒。
当然,传记式批评在考订本事的同时,不免恰恰误将作品和作者进行改写和曲解。美国哲学家亨利•亚当斯在写给自己的弟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一封信中,这样解释写作其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的初衷:“本书只不过是坟墓前的一个保护盾。我建议你也同样对待你的生命。这样,你就可以防止传记作家下手了。”我的这些努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坏了海子坟墓前的保护盾。传记搅浑诗歌,或者说,诗歌搅浑传记,都是批评的失败。所以,我在行文中添加了新批评式的圆滑:牢记Text一词的拉丁语源Texere,保持对文本的适度信任,对传记性因素的必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