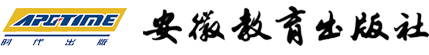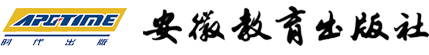―――读钟叔河先生《念楼集》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4月11日 07:16 中华工商时报
2003-4-113:21:52李传玺/文
古人云:“有大识见,才有大文章。”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先生站在“念楼”上用一种既超脱又关切的目光,糅合渊博的学识、深沉的智慧、不断的体念的结晶。因此读此书,必须格外小心,在先生是随意的引用与随意的点拨,可能就隐藏着一个玄机,特别是年轻人因根底肤浅与快餐文化构成的差距,可能稍一疏忽,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脚踏空。然后是不知所之不知所以过年前两天的上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唐元明兄打电话说,过来我送你一本好书。立即骑车奔去,原来是钟叔河老先生的《念楼集》。前一天才印出,书还没压平复,透着纸香墨香。封面白底,正中竖排集知堂字也是钟先生找人竹刻做宅名的书名,淡淡的赭黄色,右上角斜伸出一丛墨竹,由浅入深,似乎浮漾着清新的雾气,整个搭配起来,却又是那么高贵典雅落落大方。一对钟先生我是崇敬的。记得十几年前读到钟先生的《三封信》(此集未收),信中详细叙述了他与周作人的交往过程。“1958年,知堂已74岁高龄,我还只有27岁,因在湖南日报社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公职,在长沙市引车卖浆为生,但劳作之余,仍只能以读书排遣。”知堂的文章,自从9岁读到后,“我即十分爱读”,此时一个偶然的机遇知道周遐寿就是周作人后,便给八道湾的周作人写去了一封信。信中不仅表达了对周作人文章的喜爱之情,对周作人文章做出至今读来仍觉十分中肯的评价,同时表达了这样一个心愿:“虽然经过刻意搜求,先生的一些文集仍然无法看到。”“假如先生手边尚有存留的文集,无论旧印新刊,能够赐寄一册,那就足以使我欣喜万分了。”并求周作人给他写一条幅。周作人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有人说钟先生是周作人的私塾弟子,当然他自己也承认,这便是由来。而我当时的直觉是,一个27岁的右派,如此落迫,不去积极向组织靠拢争取早日脱帽,而是一心想着读书,并且读周作人的书,还给解放后已是人言人弃的周作人写信,要是当时泄露出去该要冒多大风险,即使放到现在也让人难以理解。没有对文化的真热爱,没有对求知的真性情以及由此构筑的真胆识,是无法做到这一切的。二这以后,我是见到钟先生的文章即读,并且将一些报刊中登的剪了下来,每篇文章也总是让你读出如此真胆识。但像这次这样一下拿到厚厚一大本,还是第一次。刚一拿到书,“念楼,”心中即嘀咕了一句,“念的是什么呢?”读序,原来不是我一人这样想,许多人望文生义,而钟先生的本义偏不是念什么,而是作者住在二十楼的另一种写法,就在我不知是为自己多想还是为作者机智而摇头一笑时,作者接着写道:“如果只是如此,何不径写廿楼或二十楼,岂不更为简明。”然后从“念”的本义说到“念”现在所有义项,最后归纳为用心和用脑两个方面,各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到此,每一读者都会明白,作者的“念”并不仅仅是二十楼,作者也没有躲进廿楼成一统,而是仍有所念,不仅用心用脑,而且是深沉的“爱心”、强烈的“忧愤”、已转化成本能的思维方式,这厚厚的一大本正是作者在“念楼”里这样日日“ 念”出来的。全书一百零四篇,分五部分,一为游记和曾经生活与风物的回忆;二为所编书的序或跋;三为书评;四大部分为文史随笔;五为从历史故事逸事寓言生发的精短杂文。为作者自己所编,最早为1982年,迄为去年8月,大部分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作,可说是作者这20年来各类文体代表作的囊括与荟萃。但不管是哪类文章,都透着作者特有的风格,立足历史,用自己渊博的知识,从文化的角度,怀着一腔社会责任感,以诚实的态度,对书本、对工作、对现实、对生活、对人生,冷静而又积极地去看去想,然后作独有的价值发掘,从而给人以新的视角新的启迪、新的反思;在表达方式上,随意征引,自说自话,娓娓道来,点到为止,却又往往出人意料,回味不已。他评最推崇的张岱的散文,“写人事,他不用心歌颂什么暴露什么,而爱怜哀矜之意自然流露,能感人于百载之后,发感想,他从不想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家国之忧、无常之痛时见于字里行间。”难道不是自况。比如《游离堆》,在人们游都江堰都不游离堆,而导游也不告诉你怎么去离堆时,他偏要一个人独辟蹊径、绝无仅有地去寻离堆,通过涉水身临其境的寻,真切地体味到了李冰利用地形巧夺天工的伟大创造力,看出了他为成都平原千秋万代立下的不朽功勋,也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官不论大小,要想留下千秋万世的美名,惟一的根本只在于“为老百姓做好事,必须实实在在,使一个地方的居民世世代代看得见摸得着,而不在乎搞什么形象工程,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宣传的再得力,声势再煊赫,上头的路子走得再深,当的官再大,如果失去了这一根本,仍旧“只能被归为 ‘十世为娼’一类”。比如评《李鸿章的全集》,他没有面面俱到地介绍书的内容,在简单交代了出版李鸿章全集的意义,用影印方式出版的好处之后,重点点出一般集中没有收也忽视的李鸿章的诗词,与洋务运动过程中李鸿章力主变法自强的几个主要观点,虽然前面对出版该书意义没有详尽,但至此,书的价值已完全体现出来,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与传统说法迥异的李鸿章的另一面,他的设想、他的清醒、他的坚毅、他的无奈,尤其是文章最后引出的李在甲午海战中给诸将领的一封信,对战争发展的预见,对担负责任的告诫,对我们如何正确分析那场战争的过失,认识那些人的形象,都有正本清源的作用,文章至此结束,可当我们掩卷时,我们不禁会想起以前评价的粗疏与轻率,不禁会想到那些历史学家,描述这段历史,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对这样重要的言行放过或视而不见,从而导致误判,当我出现这些联想时,我发觉作者笑了,似乎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将它们列了出来,你们看着办吧。比如第五部分“改文字”那一组,每篇皆不超过一千字,全是“学其短”的精粹之作,从典籍中抽出一段加以轻轻点染,一切那么随意,可又显得从容不迫,你不仅学到知识,学到一个老人的智慧与博学,如果说反其道而行之也是一种模仿,则你于其中更可以看到现实,没有现实的现实,其病象的由来已久。《树倒猢狲散》,一个老成语,人人皆知他的含义,有什么说头,他从庞元英《谈薮》中扯出其来历,曹咏当上秦桧亲信后,许多人皆去攀附,独妻兄不肯,想方设法让他来也不肯,秦倒了自然曹也倒,这时他才送来一篇《树倒猢狲散赋》,然后从自然现象谈此合理性以及它现在正常的比喻,就在你认为全篇可能不过如此时,文章最后一句从曹咏逼妻兄趋附引出,“难道树一大了,便有想要猢狲来爬的瘾么?”戛然而止,你一下警醒,前面所有的都是为此爆发的铺垫,而先生对世事的洞见更令你拍案叫绝。三古人云:“有大识见,才有大文章。”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先生站在“念楼”上用一种既超脱又关切的目光,糅合渊博的学识、深沉的智慧、不断的体念的结晶。因此读此书,必须格外小心,在先生是随意的引用与随意的点拨,可能就隐藏着一个玄机,特别是年轻人因根底肤浅与快餐文化构成的差距,可能稍一疏忽,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脚踏空然后是不知所之不知所以。可又正是在这里,它让我们明白了两个事理:其一是所谓洗尽铅华现本色,一般我们都理解成文风与语言,钟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它也是热烈的情怀,世事的明晰,经验的丰富,学问的精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之对观点对材料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以简搏约,深中肯綮;其二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一般我们是指美妙的意境,读钟先生的文章,它也可以说是理趣,它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充满着迷人的机智,它不是絮絮叨叨的一览无余,而是点石成金的要言不烦,它不是简单的结论,而是站在幽径前的标志,它不是寒冬中的秃枝,而是绽放着梅花的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