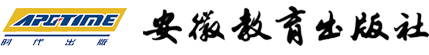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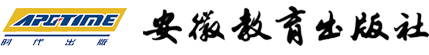
――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为例 |
[作者:网友 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675 更新时间:2007-2-2] |
钱穆先生(1895~1990)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读书淹贯经史子集四部,著述宏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是其一生著述的集成,连“总目”在内共五十四册,约一千七百万字。《全集》所收多种单行本著作,近十余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又一次推出钱先生的八卷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见到钱先生著述中最精要的部分了。 有学者将钱穆先生的著述分为三大类,即专门著作、通俗著作和介于二者之间的“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作”,专门著作中有《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等(见韩复智《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要对这类著作做一公允的评说,因识见所限,无能为力;此处只选择稍微熟悉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以下简称《论丛八》)略作讨论。《论丛八》除自序外,收论文二十六篇。“自序”作于1979年,钱穆先生在序文中述及民国二十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来研究清代学术之简况,前后近五十年,可见他对此一专题的长久关注。大致而言,钱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著述,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和《论丛》第八册最为重要。因第八册所收二十六篇论文此前不易见,更重要的是其中《〈清儒学案〉序》一篇牵涉诸多问题,故有必要对第八册作一述评;举一反三,由此亦可推想《论丛》的学术思想含量。 “学案体”及读书法 无论是《论丛八》,还是《学术史》和《国学概论》,钱穆先生在论某家之学时,常用《明儒学案》式的“学案体”或《颜氏学记》式的“学记体”方式来组织材料讨论问题。“学案体”和“学记体”虽略有差异,然皆重视采录学人的著述来显现其学术思想。钱先生在运用这种方式时,已有变通之举,那就是加强自己的判断和论述;不过,这种方式在不同的著作中表现的程度并不相同。在《国学概论》第九章中,摘录只是点到为止,在《学术史》中空间稍大,然亦受整体的学术史的结构的约制,亦不能全面展现;这种不足在《论丛八》中则得以弥补。譬如经过胡适、顾颉刚等大力表彰而“复活”的姚际恒(立方)在《学术史》中附于阎若璩毛奇龄之后,所占篇幅不过一页纸而已,而在《论丛八》中有两篇文章分别论及姚氏所著《礼记通论》和《诗经通论》;又如以编《朱子年谱》名世、作为宋明六百年理学殿军的王懋�(白田),在《学术史》中附在李穆堂之后,而在《论丛》中则有二十一页纸的长文。此种篇幅上的差异,是因各书体制和作者读书范围变化造成;这种差异的存在,也表明我们在读《学术史》时,在了解钱穆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时,不能忽略《论丛八》的价值。事实上,钱先生在写这批论文时,有扩充增补《学术史》之意。检读《论丛八》,发现钱先生在行文中至少有十五次提及《学术史》;扩充增补《学术史》之意亦多次予以明示,如关于吕留良的《吕晚村学述》,“此篇稽之《晚村文集》,撮记其生平,以附本编稼书一篇之后,并以补往年《学术史》旧著所未详。徐世昌《清儒学案》摭述张杨园、陆稼书两家著述有关晚村生平者数事,殆似未见晚村集也。余撰《学术史》时,亦已据《晚村文集》,惟今所述,与《学术史》详略互异,读者可参阅。”(第136页)《论丛八》中除十一篇与《学术史》所论人物直接对应外,另外十人也可补《学术史》之未备。 钱穆先生喜用“学案体”或“学记体”这种传统的著述体例,其实隐涵了一种读书治学方式。这种体例要求撰者从头到尾看某一学人的著述,并细加体会从而择其精要。韩复智尝记录钱先生九十三岁在素书楼授课时的言语,其中有一段涉及读书方法: 我没有什么长处,如果说有的话,就是我有恒。我读书有恒。我每天必读书,一家一家、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见前引文) 话语质朴无华,但其中却有大道理,那就是持之以恒地“一家一家、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此即虚心体察的涵泳工夫。读书,先要平心静气体会著作者的为文意旨,若先存己见和怀疑,则读书不能入其内。严耕望回忆钱穆先生关于“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演说中有一段文字可与上文比照: 读一书,先要信任他,不要预存怀疑,若有问题,读久了,自然可发现,加以比较研究;若走来就存怀疑态度,便不能学。(《治史三书》第242页) 这两段文字,其神理与《朱子语类》以及朱子在其他著述中论读书法的文字近似,钱穆先生编《朱子新学案》,将此类文字集辑一处,如“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就在其中。(《晦庵文集》卷四十八)朱子读书法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和理论价值,在中国是无人可比;钱先生是近世朱子学的最大功臣,承继并践行此法,其轨迹在《论丛八》中历历可见。《王船山孟子性善义阐释》一文,专就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一书,将其中关于阐释孟子道性善之义的文字撮列举要,在所选文字之后加上按语,此乃先倾听前贤如何说,然后以己见与前贤商量讨论,务求“透露其精神,发明其宗旨”(第362页),而在论文前后,又有放开眼界作比较之语,将船山所述与前后学人略作比较,以示此问题源流衍变。此专就王夫之而言,而针对学人的众多著述所作的“学述”,在《论丛八》中有陆桴亭、顾亭林、陆稼书、吕晚村、王白田、钱竹汀、罗罗山、朱九江、章太炎九篇。在论说王懋�(白田)的学术思想时,钱穆先生将其置入晚明以来朱子学的流衍之中考量,白田的学术活动集中在乾隆一朝,所以他“治朱子学,所信重固在义理,而其探讨之方法与途径,则一如当时之学风,主要在考据与注释之两者。”(第190页)也就是说白田以时人考据经学之法来治理学,所得甚丰;白田治朱子书外,亦旁及于考史,然“白田考史论史,率多从朱子语触发引申,非能从史籍自有超卓潜深之研究,此乃考据学者一通病。乾嘉以下清儒治经,自标以为汉儒之经学,然于古经籍及大义乃及汉儒通经致用之精神,渺不相涉,既已漫失其纲宗,徒于散末处枝节分别,以考以辨,用力甚勤,而所得实觳。”依钱先生之意,白田治朱子学,虽所得甚丰,然“自有一限量”(第202页)。读书要能入乎其内,又要能出乎其外;钱穆先生这段文字正是出乎其外的断语。我们常为大家著述中高明的断语所折服,其实此类精简的语句背后有大量的证据、史实和推导过程作为基础,而这些又不是一本书所能提供的,而是在“一家一家、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中得出的。 考据学地位的变化 以上引评说王白田的一段文字中,可看出钱穆先生对乾嘉考据之学的评价并不高。钱先生擅长考据,《先秦诸子系年》即其代表作,此书也确立了他在当时的学术界的地位;然观其一生著述,以考据见长的著作比重较小,他的理想似是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更看重的是通人之学,而不是专家。 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 〔梁〕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王�国维�先生讲历史考证,自清末迄今,无与伦比,虽然路径是第二流,但他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绩不可磨灭。考证如此,也可跻于第一流了。(分别见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42页、250页) 这两段文字足以表现钱穆先生治学的旨趣,考据之学只是治学的一种方法,倘若用力于此,亦须高远的眼光。在《论丛八》中有一文论说朱次琦(稚圭)之学,以为朱氏将学问分为经、史、掌故、性理、辞章,而独不及考据乃宏达之见,“乾嘉诸儒意欲以汉学摈宋学,遂言考据。考据乃治学中所有事,岂能自成为学?”(第316页)此文未标明写作发表年代,不知是钱先生早年文字还是晚年文字,但他对考据学的评量自三十年代以后是一贯的,以下将其三种清代学术史研究文献中重点讨论的学人依次列出,因为收录在《论丛八》中的《清儒学案序》有重要价值,亦别裁列出,以略见钱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的选材、章节设计的变化。 《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成于1928年 黄梨洲、陈乾初、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王船山、颜习斋、李恕谷、万季野、顾亭林、阎若璩、胡渭、惠栋、江永、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凌廷堪、焦循、阮元、章学诚、方植之、庄存与、刘逢禄、魏源、康有为、黄以周、俞樾、孙诒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按章目次序),成于1937年 黄梨洲(附陈乾初、潘用微、吕晚村)、王船山、顾亭林(附马�)、颜习斋李恕谷、阎潜邱毛西河(附姚立方、冯山公、程绵庄、胡东樵、顾宛溪)、李穆堂(附万孺庐、王白田、朱止泉、全谢山、蔡元凤)、戴东原(江慎修、惠栋、程易田)、章实斋(袁简斋、汪容甫)、焦里堂阮芸台凌次仲(附许周生、方植之)、龚定庵(附庄方耕、庄葆琛、刘申受、宋于庭、魏默深、戴子高、沈子敦、潘四农)、曾涤生(附罗罗山)、陈兰甫(附朱鼎甫)、康长素(附朱子襄、廖季平、谭复生) 《清儒学案》所列六十四学案(学案二 |